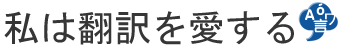- テキスト
- 歴史
Lars og Mads Mikkelsen er født med
Lars og Mads Mikkelsen er født med halvandet års mellemrum. De har gået på de samme skoler, og som børn var de hinandens bedste venner. Som voksne valgte de den samme uddannelse og blev skuespillere med et års mellemrum. Alligevel er de vidt forskellige - både personligt og som skuespillere.
Lars Mikkelsen, 36 år, er høj og spinkel. Ansigtet er smalt og markeret med skarpe kindben og intense, gråblå øjne. Og selv om han sidder så roligt og venligt i sit helt almindelige hverdagstøj, kan man godt forstå, at det netop var ham, der blev valgt til at spille hovedrollen i "Dracula" på Aalborg Teater i 1995.
Lars Mikkelsen har især koncentreret sig om teateret, siden han forlod Statens Teaterskole i 1995. Han har været med i en lang række forestillinger på bl.a. Aalborg Teater og små, eksperimenterende teatre som Bådteatret og Kaleidoskop i København, indtil han blev han fastansat for et par år siden på Det Kgl. Teater.
Mads Mikkelsen er knapt ti centimeter mindre end sin storebror og kraftigere bygget. Det halvlange, tilbagestrøgne hår og skægstubbene gør ham drenget og lidt fræk at se på. Suppleret med et par flirtende, brune øjne, en bred og følsom mund og høje kindben ligner han den perfekte ugebladsopskrift på en rigtig "hjerteknuser" og heltefigur.
Da teaterchef Lars Kaalund satte "Romeo og Julie" op på Østre Gasværk, var det Mads, der fik rollen som Romeo. Han er tilknyttet kredsen omkring Dr. Dante og Østre Gasværk. Men siden afgangen fra skuespillerskolen på Århus Teater i 1996 har han især koncentreret sig om at lave film og er i dag én af Nicolas Winding Refns "faste" skuespillere.
MM: »Der er nogle former for teater, jeg bare ikke gider. Jeg synes f. eks. det er uinteressant at spille Holberg, Ipsen og Shakespeare i traditionel forstand. Det er ikke fordi, jeg har noget imod klassikere, det er bare så sjældent, de bliver opført på en måde, der vedkommer mig. Det drukner som regel i teknik og "lad os nu endelig være helt stille, når vi spiller Shakespeare, for det er sådan nogle fine ord!" Men Shakespeare er jo hamrende beskidt! Hvorfor skal det absolut være så fint og højstemt? Jeg vil spille teater med en form for liv i, som jeg kan identificere mig med.«
LM: »Jeg orker heller ikke de dér stive formstudier, der bliver lavet så mange af. Jeg har selv været igennem en stribe af dem. De er et tegn på, at inderligheden ikke har gode kår i dansk teater for øjeblikket. Det afgørende er jo at berøre publikum, frem for at de bare betragter noget oppe på scenen.«
Ordene er det vigtige
Men det er vel næppe tilfældigt, at du spiller på Det Kgl. Teater, mens Mads hører til i kredsen omkring Dr. Dante og Østre Gasværk?
»I starten må man jo bare tage, hvad man kan få. Men nej, selvfølgelig er det ikke helt tilfældigt.«
MM: »Det handler meget om sprog. Jeg valgte jo allerede tidligt at høre til dem, der ikke kan tale t-y-d-e-l{mdash}i-g-t, men som snakker som almindelige mennesker nu gør,« siger han med det bredeste, selvironiske grin.
LM: »Jeg er meget inspireret af nogle af de gamle skuespillere inde på teatret. Hvorfor virker det bare, når de går på scenen? Selvfølgelig har de en masse erfaring, men det handler også om, at de har mod til at lade deres rolle være båret af ordene. Det er en form for minimalisme, som - når den mestres - er ultimativ. Men vejen derhen er belagt med mange krukkerier.«
MM: »Jeg er lige så interesseret i ordet som Lars. Men for mig er det utroligt vigtigt at ramme figuren så ægte og tæt på virkeligheden som overhovedet muligt. Det er det, jeg forfølger mest ihærdigt. Det er vist dét, man kalder method acting, hvor man stræber efter at "blive" figuren - uden at jeg skal forsøge at gøre mig klog på, hvad method acting er.«
Hinandens kritikere
Hvor ligger jeres største ligheder?
MM: »Vi er begge to lige meget til fals for poesien i teatret. I sidste ende er det jo den, der rører os.«
LM: »Og så er vi arbejdende skuespillere. Konstant søgende efter at blive bedre. Ingen af os vil lade sig nøje."
Kan I bruge hinanden i den proces? Er I hinandens hårde kritikere?
LM: »Ikke hårde. Men vi bruger hinanden, ja. Jeg brugte f. eks. Mads, da jeg lavede "Edderkoppen". Jeg var ikke kommet med på den dér bølge med at dyrke autenciteten i skuespillet, og det irriterede mig. Men ved hjælp af Mads har jeg pejlet mig ind på, hvad det egentlig er, og hvorfor det er så interessant.«
MM: »Og da jeg lavede "Romeo og Julie" på Gasværket, brugte jeg Lars omkring det sproglige arbejde. Han har en teknik, jeg godt kunne lære noget af klangmæssigt og tydelighedsmæssigt.«
LM: »Men der hvor vi bruger hinanden aller mest, det er i virkeligheden til at mane tvivlen i jorden. Som skuespiller er man altid plaget af tvivl: Er det nu godt nok? Gør jeg det rigtige?«
De to brødre er de første skuespillere i familien. De har ingen andre søskende og er vokset op i en politisk familie med kommunistisk baggrund. Morfaderen fik dem allerede tidligt til at læse russisk litteratur og Hans Scherfig.
Moderen var sygehjælper, faderen var bankmand, men blev ansat i fagbevægelsen som ganske ung.
LM: »Det var ikke noget kulturelt hjem. Men der var masser af fantasi og gode historier. Vi har f. eks. hørt radiospil fra vi var ganske små. Min far optog de bedste af de gode, gamle hørespil fra 50'erne, "Mordets melodi" og "Gregory-mysteriet" og den slags, som lagde gaderne øde. Vi hørte dem altid, når vi var i sommerhuset, så sad hele familien samlet omkring kassettebåndoptageren og lyttede. «
MM: »Jeg kan recitere hele "Mordets melodi". Jeg hørte den to gange om dagen i et helt år. Til sidst kunne jeg alle stemmerne, alle lydene udenad.«
LM: »Senere fik vi det på samme måde med Monthy Python. Vi havde alle deres plader og kunne dem udenad. Vi var ulidelige at være sammen med.«
En isklump i hovedet
Hvad er jeres første erindring om den anden?
MM: »Der var engang, hvor Lars fik en isklump i hovedet. Det var dengang vi boede på Østerbro.«
LM: »Hold kæft, det er præcis den samme episode, jeg tænker på! Jeg var så glad og skulle bare ned og lege, og næppe var jeg trådt ud i gården, før jeg fik en isklump lige i snotten og fik en ordenligt blodtud.«
MM: »Lars kom op og var meget ked af det. Så måtte jeg lige ned og smadre dem alle sammen, fordi de havde været lede ved ham. Og så fik jeg selvfølgelig også en isklump i hovedet.«
Men det var dig, lillebroderen, der var den beskyttende?
LM: »Mads var altid den udfarende. Jeg var mere skrøbelig, sådan var det bare. Kan du huske i skolen, i én af de første klasser - engang var der én fyr, der sparkede...«
MM: »...Træsko-Jens, ja!«
LM: »...sparkede mig lige i nosserne med sine træsko. Så fik han bank af dig.«
MM: »Han sparkede også mig. Men jeg nægtede at vise, at det gjorde ondt.«
LM: »Jeg var typen, der knækkede sammen med det samme og sagde AV!«
MM: »I mange situationer var rollerne byttet om dengang. Selv om jeg som lillebror var fysisk mindre end dig.«
LM: »Jeg var for tynd og ranglet, derfor turde jeg ikke slås. Men det kom jo hen ad vejen. En dag slog jeg fra mig, og siden var der ingen, der rørte mig. Men jeg har aldrig haft lyst til at slå. Det er noget med et temperament, som jeg havde svært ved at styre.«
MM: »Du var nok mere usikker end jeg, og det var meget tydeligt dengang. Det betød f. eks. utroligt meget for Lars, om han var med i gruppen. Jeg var bedøvende ligeglad, og hvis der var en gruppe, jeg gerne ville med i, skulle jeg nok sørge for at komme det.«
Det mørkeblå værelse
Hvad med kærester?
LM: »Det var ikke noget problem, for vi havde ikke samme smag.«
MM: »Og jeg kom meget sent i gang, fordi jeg var så optaget af sport. Da jeg fik øjnene op for pigerne, var det nærmest fra den ene dag til den anden. Lars havde en laaaaang teenage-periode med mange kærester. Og et værelse, der blev malet mørkeblåt, det var mest noget med depressiv musik og digte og sove 26 timer i døgnet.«
LM: »Jeg var konstant ulykkeligt forelsket. I mange år fandt jeg grobund i de mest depressive følelser. Det er først inden for de seneste år, det for alvor er lettet..«
Hvad tænkte du om Lars, når han sad inde i sit mørkeblå værelse og var depressiv og skrev digte og hørte klassisk musik?
MM: »Der var en klar brist i vores forhold i den periode. Vi havde intet til fælles - ud over at spille lidt håndbold sammen i ny og næ. I øvrigt spillede Lars elendigt dengang, mens jeg brugte hele mit liv på at dyrke sport. Men jeg havde meget svært ved at forstå, hvad det handlede om. Faktisk var jeg provokeret, fordi jeg syntes, han bare dyrkede sådan en påtaget "Weltschmertz".«
LM: »Jamen, det gjorde jeg jo også!«
En total klovnerøv
MM: »Jeg var en total klovnerøv. Jeg var overbevist om, at pigerne ville finde det enormt interessant og blive vilde med mig, hvis jeg f. eks. turde æde en masse ulækre ting. Det var altid noget med gang i den og fis og ballade. Jeg havde helt vildt meget energi og var - og er måske stadig - sådan én, man havde lyst til at give en ordentlig én på lampen. I gymnasiet var det noget med at ryge og drikke øl. Og jeg opdagede, at jeg var i stand til at bringe mig selv i fokus hele tiden og blive set af pigerne. Det har nok været kendetegnende for mit liv lige siden.«
LM: »Jeg søgte indhold og substans. Var optaget af kampen for hvalerne og dén slags. Reelt var det jo noget med at holde livet på to skridts afstand og digte om det i stedet for. Fordi jeg fandt det for svært at være til stede i nuet.
Hvad syntes du om Mads dengang?
LM: »At han var dybt overfladisk og ikke forstod, hvad livet handlede om. Ha!«
Hvornår fandt I så hinanden igen?
MM: »Efter gymnasietiden, tror jeg.«
LM: »Jeg blev først student året efter Mads. Faktisk gik jeg fem år i gymnasiet, fordi jeg røg så meget hash. Jeg blev smidt ud to gange.«
MM: »Til gengæld fik du en fremragende eksamen. Jeg bestod kun lige med nød og næppe.«
Det må have påvirket jer, at lillebror blev student før storebror?
LM: »Ja, det var ikke særlig sjovt. Men uden at komme for meget ind på det, så var t
Lars Mikkelsen, 36 år, er høj og spinkel. Ansigtet er smalt og markeret med skarpe kindben og intense, gråblå øjne. Og selv om han sidder så roligt og venligt i sit helt almindelige hverdagstøj, kan man godt forstå, at det netop var ham, der blev valgt til at spille hovedrollen i "Dracula" på Aalborg Teater i 1995.
Lars Mikkelsen har især koncentreret sig om teateret, siden han forlod Statens Teaterskole i 1995. Han har været med i en lang række forestillinger på bl.a. Aalborg Teater og små, eksperimenterende teatre som Bådteatret og Kaleidoskop i København, indtil han blev han fastansat for et par år siden på Det Kgl. Teater.
Mads Mikkelsen er knapt ti centimeter mindre end sin storebror og kraftigere bygget. Det halvlange, tilbagestrøgne hår og skægstubbene gør ham drenget og lidt fræk at se på. Suppleret med et par flirtende, brune øjne, en bred og følsom mund og høje kindben ligner han den perfekte ugebladsopskrift på en rigtig "hjerteknuser" og heltefigur.
Da teaterchef Lars Kaalund satte "Romeo og Julie" op på Østre Gasværk, var det Mads, der fik rollen som Romeo. Han er tilknyttet kredsen omkring Dr. Dante og Østre Gasværk. Men siden afgangen fra skuespillerskolen på Århus Teater i 1996 har han især koncentreret sig om at lave film og er i dag én af Nicolas Winding Refns "faste" skuespillere.
MM: »Der er nogle former for teater, jeg bare ikke gider. Jeg synes f. eks. det er uinteressant at spille Holberg, Ipsen og Shakespeare i traditionel forstand. Det er ikke fordi, jeg har noget imod klassikere, det er bare så sjældent, de bliver opført på en måde, der vedkommer mig. Det drukner som regel i teknik og "lad os nu endelig være helt stille, når vi spiller Shakespeare, for det er sådan nogle fine ord!" Men Shakespeare er jo hamrende beskidt! Hvorfor skal det absolut være så fint og højstemt? Jeg vil spille teater med en form for liv i, som jeg kan identificere mig med.«
LM: »Jeg orker heller ikke de dér stive formstudier, der bliver lavet så mange af. Jeg har selv været igennem en stribe af dem. De er et tegn på, at inderligheden ikke har gode kår i dansk teater for øjeblikket. Det afgørende er jo at berøre publikum, frem for at de bare betragter noget oppe på scenen.«
Ordene er det vigtige
Men det er vel næppe tilfældigt, at du spiller på Det Kgl. Teater, mens Mads hører til i kredsen omkring Dr. Dante og Østre Gasværk?
»I starten må man jo bare tage, hvad man kan få. Men nej, selvfølgelig er det ikke helt tilfældigt.«
MM: »Det handler meget om sprog. Jeg valgte jo allerede tidligt at høre til dem, der ikke kan tale t-y-d-e-l{mdash}i-g-t, men som snakker som almindelige mennesker nu gør,« siger han med det bredeste, selvironiske grin.
LM: »Jeg er meget inspireret af nogle af de gamle skuespillere inde på teatret. Hvorfor virker det bare, når de går på scenen? Selvfølgelig har de en masse erfaring, men det handler også om, at de har mod til at lade deres rolle være båret af ordene. Det er en form for minimalisme, som - når den mestres - er ultimativ. Men vejen derhen er belagt med mange krukkerier.«
MM: »Jeg er lige så interesseret i ordet som Lars. Men for mig er det utroligt vigtigt at ramme figuren så ægte og tæt på virkeligheden som overhovedet muligt. Det er det, jeg forfølger mest ihærdigt. Det er vist dét, man kalder method acting, hvor man stræber efter at "blive" figuren - uden at jeg skal forsøge at gøre mig klog på, hvad method acting er.«
Hinandens kritikere
Hvor ligger jeres største ligheder?
MM: »Vi er begge to lige meget til fals for poesien i teatret. I sidste ende er det jo den, der rører os.«
LM: »Og så er vi arbejdende skuespillere. Konstant søgende efter at blive bedre. Ingen af os vil lade sig nøje."
Kan I bruge hinanden i den proces? Er I hinandens hårde kritikere?
LM: »Ikke hårde. Men vi bruger hinanden, ja. Jeg brugte f. eks. Mads, da jeg lavede "Edderkoppen". Jeg var ikke kommet med på den dér bølge med at dyrke autenciteten i skuespillet, og det irriterede mig. Men ved hjælp af Mads har jeg pejlet mig ind på, hvad det egentlig er, og hvorfor det er så interessant.«
MM: »Og da jeg lavede "Romeo og Julie" på Gasværket, brugte jeg Lars omkring det sproglige arbejde. Han har en teknik, jeg godt kunne lære noget af klangmæssigt og tydelighedsmæssigt.«
LM: »Men der hvor vi bruger hinanden aller mest, det er i virkeligheden til at mane tvivlen i jorden. Som skuespiller er man altid plaget af tvivl: Er det nu godt nok? Gør jeg det rigtige?«
De to brødre er de første skuespillere i familien. De har ingen andre søskende og er vokset op i en politisk familie med kommunistisk baggrund. Morfaderen fik dem allerede tidligt til at læse russisk litteratur og Hans Scherfig.
Moderen var sygehjælper, faderen var bankmand, men blev ansat i fagbevægelsen som ganske ung.
LM: »Det var ikke noget kulturelt hjem. Men der var masser af fantasi og gode historier. Vi har f. eks. hørt radiospil fra vi var ganske små. Min far optog de bedste af de gode, gamle hørespil fra 50'erne, "Mordets melodi" og "Gregory-mysteriet" og den slags, som lagde gaderne øde. Vi hørte dem altid, når vi var i sommerhuset, så sad hele familien samlet omkring kassettebåndoptageren og lyttede. «
MM: »Jeg kan recitere hele "Mordets melodi". Jeg hørte den to gange om dagen i et helt år. Til sidst kunne jeg alle stemmerne, alle lydene udenad.«
LM: »Senere fik vi det på samme måde med Monthy Python. Vi havde alle deres plader og kunne dem udenad. Vi var ulidelige at være sammen med.«
En isklump i hovedet
Hvad er jeres første erindring om den anden?
MM: »Der var engang, hvor Lars fik en isklump i hovedet. Det var dengang vi boede på Østerbro.«
LM: »Hold kæft, det er præcis den samme episode, jeg tænker på! Jeg var så glad og skulle bare ned og lege, og næppe var jeg trådt ud i gården, før jeg fik en isklump lige i snotten og fik en ordenligt blodtud.«
MM: »Lars kom op og var meget ked af det. Så måtte jeg lige ned og smadre dem alle sammen, fordi de havde været lede ved ham. Og så fik jeg selvfølgelig også en isklump i hovedet.«
Men det var dig, lillebroderen, der var den beskyttende?
LM: »Mads var altid den udfarende. Jeg var mere skrøbelig, sådan var det bare. Kan du huske i skolen, i én af de første klasser - engang var der én fyr, der sparkede...«
MM: »...Træsko-Jens, ja!«
LM: »...sparkede mig lige i nosserne med sine træsko. Så fik han bank af dig.«
MM: »Han sparkede også mig. Men jeg nægtede at vise, at det gjorde ondt.«
LM: »Jeg var typen, der knækkede sammen med det samme og sagde AV!«
MM: »I mange situationer var rollerne byttet om dengang. Selv om jeg som lillebror var fysisk mindre end dig.«
LM: »Jeg var for tynd og ranglet, derfor turde jeg ikke slås. Men det kom jo hen ad vejen. En dag slog jeg fra mig, og siden var der ingen, der rørte mig. Men jeg har aldrig haft lyst til at slå. Det er noget med et temperament, som jeg havde svært ved at styre.«
MM: »Du var nok mere usikker end jeg, og det var meget tydeligt dengang. Det betød f. eks. utroligt meget for Lars, om han var med i gruppen. Jeg var bedøvende ligeglad, og hvis der var en gruppe, jeg gerne ville med i, skulle jeg nok sørge for at komme det.«
Det mørkeblå værelse
Hvad med kærester?
LM: »Det var ikke noget problem, for vi havde ikke samme smag.«
MM: »Og jeg kom meget sent i gang, fordi jeg var så optaget af sport. Da jeg fik øjnene op for pigerne, var det nærmest fra den ene dag til den anden. Lars havde en laaaaang teenage-periode med mange kærester. Og et værelse, der blev malet mørkeblåt, det var mest noget med depressiv musik og digte og sove 26 timer i døgnet.«
LM: »Jeg var konstant ulykkeligt forelsket. I mange år fandt jeg grobund i de mest depressive følelser. Det er først inden for de seneste år, det for alvor er lettet..«
Hvad tænkte du om Lars, når han sad inde i sit mørkeblå værelse og var depressiv og skrev digte og hørte klassisk musik?
MM: »Der var en klar brist i vores forhold i den periode. Vi havde intet til fælles - ud over at spille lidt håndbold sammen i ny og næ. I øvrigt spillede Lars elendigt dengang, mens jeg brugte hele mit liv på at dyrke sport. Men jeg havde meget svært ved at forstå, hvad det handlede om. Faktisk var jeg provokeret, fordi jeg syntes, han bare dyrkede sådan en påtaget "Weltschmertz".«
LM: »Jamen, det gjorde jeg jo også!«
En total klovnerøv
MM: »Jeg var en total klovnerøv. Jeg var overbevist om, at pigerne ville finde det enormt interessant og blive vilde med mig, hvis jeg f. eks. turde æde en masse ulækre ting. Det var altid noget med gang i den og fis og ballade. Jeg havde helt vildt meget energi og var - og er måske stadig - sådan én, man havde lyst til at give en ordentlig én på lampen. I gymnasiet var det noget med at ryge og drikke øl. Og jeg opdagede, at jeg var i stand til at bringe mig selv i fokus hele tiden og blive set af pigerne. Det har nok været kendetegnende for mit liv lige siden.«
LM: »Jeg søgte indhold og substans. Var optaget af kampen for hvalerne og dén slags. Reelt var det jo noget med at holde livet på to skridts afstand og digte om det i stedet for. Fordi jeg fandt det for svært at være til stede i nuet.
Hvad syntes du om Mads dengang?
LM: »At han var dybt overfladisk og ikke forstod, hvad livet handlede om. Ha!«
Hvornår fandt I så hinanden igen?
MM: »Efter gymnasietiden, tror jeg.«
LM: »Jeg blev først student året efter Mads. Faktisk gik jeg fem år i gymnasiet, fordi jeg røg så meget hash. Jeg blev smidt ud to gange.«
MM: »Til gengæld fik du en fremragende eksamen. Jeg bestod kun lige med nød og næppe.«
Det må have påvirket jer, at lillebror blev student før storebror?
LM: »Ja, det var ikke særlig sjovt. Men uden at komme for meget ind på det, så var t
0/5000
拉爾斯和爾森是出生與一個半年。他們去了同一所學校,和孩子們他們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作為成年人他們選擇了同樣的訓練,每隔一年的演員。他們卻非常不同,個人和作為演員。拉爾斯 · 凱爾森,36,又高又苗條。面對的是窄,並標明瞭鋒利的顴骨和激烈,灰藍色的眼睛。即使他是如此平靜和友好普通平凡的衣服,一可以理解,這正是他被選為 1995 年在奧爾堡劇院的 《 吸血僵屍 》 中扮演主角。拉爾斯 · 凱爾森已主要集中在劇院,自從他離開劇院丹麥國立學院于 1995 年。他一直參與廣泛的演出,除其他外。奧爾堡劇院和小,實驗劇院作為 Bådteatret 和萬花筒在哥本哈根,直到他,他被錄用為前幾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劇院。麥斯爾森是幾乎十釐米小於其大哥和更健壯。半長、 背成型的頭髮和鬍鬚 stubbene 使他的孩子氣和略有淘氣地看看。輔以幾個輕浮,棕色的眼睛、 廣泛和敏感的嘴和高顴骨看起來好像他是完美的真正的"萬人迷"和英雄人物的良方。當劇院經理 Lars Kaalund 設置在 Østre Gasværk 的 《 羅密歐與茱麗葉 》 時,這是福克斯,得到了羅密歐的角色。他是與周圍博士 Dante 和 Østre Gasværk 的圓圈。但自 1996 年在奧爾胡斯劇院演員學校的退出,他主要集中在製作電影和今天 Nicolas 繞組 Refns 之一"固定的"演員。MM: ' 有某種形式的劇院,我只是不打擾。我想舉個例子。它是無趣在傳統意義上發揮霍爾,易普森和莎士比亞。它是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反對的經典,它是只是很少,他們會對我有影響的方式列出。通常,它淹沒在技術和"讓我們現在終於是完全沉默當我們扮演莎士比亞,因為那是一些如何動聽說話!"但莎士比亞是髒的衝擊!為何要如此精細和誇張?我會玩劇院與形式的生活,我可以確定我的.LM:» 第一和那裡的獸人剛性形式研究,將會創建很多。我自己經歷過一系列的他們.他們是這方面的跡象親密並沒有良好的條件在丹麥劇院此刻。要緊的是要打動觀眾,而不是只是考慮的東西,在舞臺上.的話,很重要的但是它不完全是巧合而屬於中博士 Dante 和 Østre Gasværk 圈的 Mads 發揮在哥本哈根皇家劇院嗎?» 在開始的時候,一隻是必須採取我們能得到什麼。但不,當然它不是完全隨機。MM: ' 這是很多關於語言。我選擇了已經早聽到的那些人,不可以說 t-y-d-e-l {-纜線} i-g-t,但說話像普通的人現在正在做,"他說帶最寬、 謙遜的笑容。LM: ' 我很鼓舞,一些在劇院裡面的老演員。只是當他們在舞臺上,為什麼不是?當然,他們有大量的經驗,但這也是對他們有勇氣,讓他們的角色應由詞的事實。它是一種極簡主義,這當梅斯特-是最終的。但去那兒的路上覆蓋著很多瓶.'MM: 我只是作為興趣作為 Lars 詞。但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此真實和貼近現實盡可能打圖。這就是我最積極。它表明你稱為代理方法,力爭"是"形狀-如果不是這樣,我必須設法讓我聰明上什麼方法是代理.'對方的批評哪裡是你最大的相似之處?MM:» 我們都等於失真在劇院的詩歌。最後,它就是那個觸動著我們.LM: 所以我們都是演員。不斷追求變得更好。我們沒有一個人想要小心"。你可以使用對方的過程嗎?在對方的激烈批評者?LM: ' 不艱難。但我們用彼此,的。我用 eg。麥斯,當我在做"蜘蛛"。不是在培養的真實性在劇中,波,它讓我心煩。但使用 Mads 我對表我它到底是什麼,以及為什麼它是如此有趣。MM: 當 《 羅密歐與茱麗葉 》 在煤氣廠制時我使用 Lars 圍繞語言工作。他有一種技術,可以從 klangmæssigt,他顯然把.'LM:» 但我們最使用每個其他阿勒,它事實上是變戲法似地懷疑。作為一個演員總是疑慮所困擾: 是它不夠好嗎?我做它正確嗎? '這兩兄弟是在家庭中的第一個演員。他們有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共產黨的背景與政治家庭中長大。他的外祖父早早他們讀俄國文學和漢斯 Scherfig。母親護理助理,她的父親是一位銀行家,但都從事工會運動在很年輕的時候。LM: ' 這不是一個文化的家。但有很多的想像力和好的故事。例如,我們有。從我們聽到的收音機遊戲是相當小的。我父親記錄最好的從好,老廣播劇 50 多歲,"旋律"和"葛列格里-神秘",諸如此類的事情,一樣空無一人的街道。我們聽見他們總是,當我們在房子裡,所以全家人圍著答錄機和坐聽了。«MM: ' 我能背誦整個"旋律"。我聽了一天兩次,整整一年。最後我可能所有的聲音,所有的聲音由心.'LM: ' 我們後來在報館 Python 同樣的方式。我們有他們所有的盤子也可以用他們的心。我們都忍不住在一起.一大塊冰的頭你第一次對方的記憶是什麼?MM: 當時當 Lars 得到一塊冰的頭。就在那時我們住在 Østerbro.'LM: ' 關了,我們那是完全相同的情節,認為的!我很快樂,只是不得不下來,玩,和幾乎不了我走進院子裡之前我有一大塊, 冰在 snotten 權利並且有正確 blodtud.'MM:» Lars 走過來,很抱歉.然後我直了和他們在一起,因為他們已經粉碎使他厭惡的。然後我當然也是一大塊冰的頭.'但它就是你,是保護性的小弟弟嗎?LM:» 狐狸始終是驅動力。我更脆弱,這就是唯一。你還記得在學校裡,在第一堂課之一-很久很久以前,那裡是一個傢伙踢......'MM:»...木屐 Jens 啊! 'LM:»...踢了我與他木屐 nosserne 的權利。所以他有很多錢的你.'MM: 他太踢我。但我拒絕讓它傷害.'LM: ' 我是那種搶購與相同並說呦! 'MM: 在許多情況下角色顛倒在那個時候。雖然我喜歡弟弟是身體比你小得多.LM: ' 我是太薄,高高瘦瘦,因此,敢。但它來了,當然,前進的道路。我搭的我,和因為他也沒有讓我感動的一天。但我從來沒有打的衝動。這是一種脾性,,好不容易控制.'MM: ' 你可能比我更不確定,它在當時是很清楚。這意味著為例。數量驚人的拉爾斯,他是否已列入集團。我麻木冷漠,和如果有的話,一群我想列入,我一定要得到它.暗藍色的房間裡男朋友怎麼樣?LM: ' 這是沒有問題,因為我們沒有同樣的口味 '。MM: 和我很晚才來在過程中,是因為我如此著迷這項運動。為女孩的眼睛的時候,它是幾乎從某一天,到下一步。Lars 座青少年時期有很多女朋友。一個房間,被漆成暗藍色,它是主要的事抑鬱的音樂、 詩歌和睡眠 26 小時一天.'LM: ' 不斷高興在愛中。多年來我發現肥沃的土壤中最壓抑的感情。只有在過去的幾年之內,感覺真的很舒服。 '。你在想什麼關於 Lars,當他坐在他暗藍色的房間裡,抑鬱,並寫了詩,聽到古典音樂?MM: ' 有時期在我們的關係是一個明確的缺陷。我們沒有什麼共同之處 — — 在一起玩一個小手除了球時不時。順便說一句演奏的 Lars 悲慘回到那時,雖然我花了我整個的生命上這項運動。卻很難理解它是關於什麼。其實我是挑起,以為他只是培養這種假設"Weltschmertz".CH: 嗯,我的確! '總 klovnerøvMM: 我是總的 klovnerøv。我確信女孩如果,會覺得它非常有趣並得到野生和我一起我如。敢不敢吃噁心的東西很多。它總是有點隨時間和 fis 和歌謠。我有很多的能量,是絕對野生-和也許仍然是這樣一個人,你有欲望,使一個合適上的油燈。在高中的時候,它是與吸煙和喝啤酒的東西。我發現能夠讓自己在集中所有的時間和看到的女孩。它可能一直是我生活的標誌.'LM:» 我搜索的內容和實質。正忙著爭取鯨魚和諸如此類的事情。事實上,它是東西反而繼續生活在距離和詩關於它的兩個步驟。因為我發現它太難活在當下。什麼你想到 Mads 回來然後呢?LM: ' 他是非常膚淺和不明白生活是什麼有關。哈哈! '何時發現在看到對方再次?MM: 高中畢業後,我認為。LM: ' 我是第一的學生一年後 Mads。實際上我去五年在高中的時候,因為我抽煙太多的雜草。我被拋出兩倍。"MM: ' 你是另一方面,得到優良的考試。我僅包括狹。"它必須影響你,畢業前的大哥哥,小弟弟?LM: ' 是啊,它不是特別有趣。但沒有得到太多了,然後是 t
翻訳されて、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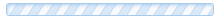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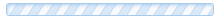
拉斯和米克爾森出生時一年半的時間。他們都去了同一所學校,並作為孩子,他們彼此最好的朋友。作為成年人,他們選擇了同樣的培訓,並投中一年的時間間隔。然而,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個人和作為演員拉爾斯·米克爾森,36歲,身材修長。面對的是窄,標有尖銳的顴骨和激烈的,灰藍色的眼睛。而且即使他坐在安靜而友好的他普通平凡的衣服,就可以很好的理解,這是誰,他被選為發揮帶頭“吸血鬼”在奧爾堡劇院在1995年拉爾斯米克爾森都集中在戲劇,因為他離開了國家大劇院學校在1995年,他曾參與過各種各樣節目,除其他外,奧爾堡大劇院和小劇場實驗作為Bådteatret和萬花筒在哥本哈根直到他,他被長期聘用,幾年前在皇家。劇院米克爾森比他哥哥越來越強建勉強10厘米。半長的頭髮回茬,並讓他的孩子氣,有點調皮一下。輔以一些輕浮,棕色的眼睛,廣泛而敏感的嘴,高顴骨,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完美的雜誌配方真正的“萬人迷”,相當的身影。作為影院經理拉爾斯Kaalund把“羅密歐與朱麗葉”上東煤氣廠,是的Mads,誰把羅密歐的作用。他隸屬於各地但丁博士和東煤氣廠圈。但是,由於戲劇學校在奧胡斯劇院於1996年退出,他專注於拍電影,是當今尼古拉斯的一個繞組雷弗恩的“真實”的演員。MM:“有一些形式的戲劇,我只是不打擾。我認為F。例,是無趣的打霍爾伯格,易普森和莎士比亞傳統意義上的。這並不是因為我對經典任何東西,它只是如此罕見,它們都建在我所關心的一種方式。它通常在淹沒技術,“我們現在終於完全平靜,當我們玩莎士比亞,因為這是怎樣的一些好話!” 但莎士比亞的怦臟!為什麼它應該有如此精細和華而不實?我會玩戲劇與生活的一種形式,我可以辨認“。LM:“我有精力,也正在作出這麼多的剛性存在形式的研究。我本人也經歷了許多。它們是強烈的需求不會有丹麥劇院的時刻了良好的條件一個標誌。重要的是觸摸的觀眾,而不是僅僅看到的東西在舞台上。“ 這句話是很重要的,但它是很難,你在皇家發揮巧合。劇院,而屬於的Mads圍繞但丁博士和煤氣廠東圓?“一開始,你只需要採取什麼你可以得到的。但是,沒有,當然這並非巧合。“ MM:“這是非常關注的語言。我選擇了早聽那些誰也不能說tydel {} mdash IGT,但普通老百姓現在做的,“他說,與最廣泛的,自我嘲諷的笑容。LM:“我感到非常受一些啟發老演員在劇場。為什麼他們上場只是當不是嗎?當然,他們有很多經驗,但它也是他們有勇氣離開自己的作用,由字攜帶。這是極簡主義的一種形式,它-當它被掌握-是最終的。但途中有塗有不少火鍋農場“。MM:“我只是在單詞作為拉爾斯的興趣。但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打圖如此的真實和貼近現實的可能。這就是我追求的最大力。這顯示了什麼叫做方法演技,在那裡你努力“成為”人物-雖然我必須設法讓我對明智的方法是什麼演技是“。對方的批評哪裡是你最大的相似之處?MM:“我們是同樣都以詩歌在劇場的接縫。到底它是一個觸動我們。“ LM:“因此,我們正在努力的演員。不斷追求變得更好。我們沒有人會滿意。“ 你可以用對方的過程中被對方苛刻的批評?LM:“。不難但我們互相利用,是我用˚F前的Mads當我做”蜘蛛“。我沒來的波有培養真實性在劇中,這惹惱了我。但是,我的Mads我pejlet在它是什麼和為什麼它是如此有趣。“ MM“當我做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在煤氣廠,我花了約拉爾斯語言的工作,他有技術,我很可能學到一些東西,從聽覺和清晰度因“。LM:“但是在這裡我們使用彼此很大部分,這是事實上,喚起在地懷疑作為一個演員,你總是困擾著疑問:??它是足夠好的我這樣做是正確的“ 。兩兄弟是在家庭中的第一個演員,他們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長大。一個政治家庭,一個共產主義背景的祖父早讓他們讀俄羅斯文學和漢斯Scherfig。他的母親是一名護士助理,他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而是加入了工會運動作為一個年輕人。LM:“這不是一個文化的家園。但也有很多的想像力和良好的故事。我們有f例。聽說廣播劇,因為我們是非常小的。我的父親帶最好的50年代的好老廣播劇的,“Mordets旋律”和“格雷戈里-神秘”之類的東西放在冷清的街道。我們聽到他們總是,當我們在山寨,然後坐在圍著錄音機全家,並聽取。“ MM:“我能背誦整”Mordets的旋律“。一天我聽到了兩次了整整一年。最後,我會所有的聲音,所有的聲音通過心臟。“ LM:“後來我們得到了相同的方式與Monthy Python的。我們都有自己的盤子,知道他們通過心臟。我們無法忍受的是與“ 冰的頭部腫塊是什麼其他的你的第一個記憶是什麼?MM:“曾經有一段時間了拉斯冰的頭部腫塊的時候。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住在哥本哈根協議“。LM:“閉嘴,這是完全一樣的情節,我覺得!我很高興,只是來打,而且幾乎沒有我走進了院子之前,我得到了冰權snoting一個腫塊,妥善得到了鼻血。“ MM:“拉爾斯過來了,很不高興。所以我只好直降,粉碎他們一起,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找他。。後來才知道,當然,冰在他的頭上也有疙瘩“ ,但它是你,小兄弟,誰是保護?LM:“的Mads總是傳出。我還是比較脆弱的,所以這是正義的。你在學校裡還記得,在第一類中的一個-曾經有一個傢伙誰踢......“ MM:“......木屐-延斯,是的!” LM:“......踢我的球,他的木屐。然後,你自己的銀行“。MM:“他踢我了。但我拒絕,以表明它受到傷害“。LM:“我是誰打破了,立即說:AV”的類型!MM:“在很多情況下,角色互換即可。雖然我喜歡的小哥哥身體比你小。“ LM:“我太細而高挑,所以我不敢打。但它得到了去。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既然沒有人讓我感動。但我從未有過的衝動擊敗。這是一個什麼脾氣,我發現它很難管理“。MM:“你可能更不確定,比我,這是很清楚的話。這意味著F。例拉爾斯令人難以置信,如果他是在一組。我麻木的關懷,如果有一組我想要的,我也許應該確保得到它。“ 漆黑的房間裡什麼男朋友?LM:“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沒有一樣的味道“ MM:“我來得很晚,因為我是如此忙碌的運動。當我意識到的女孩,這幾乎是從一天到另一個。拉斯有一個十幾歲的laaaaang時期有許多愛好者。而這被漆成深藍色的房間,這是任何東西抑鬱音樂和詩歌睡了26天時間“。LM:“我愛上不斷不高興。多年來,我在最壓抑的情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它只是在最近幾年,它具有真正的放心..“ 什麼是你想拉爾斯時,他正坐在他的黑暗房間,鬱悶,寫詩歌,聽古典音樂?MM:“有一個明確的缺陷在我們的在週期的關係。我們有沒有共同點-除了玩一些手球一起飄飛。順便打了拉斯慘時間,而我花了我的整個生命體育運動。但我有一個很難理解究竟是什麼了。其實,我被激怒了,因為我以為他只是養成了這樣一個堅定的“Weltschmertz”。“ LM:“好吧,我做得很好呢!” 一共有klovnerøv MM:“我是一個總的klovnerøv。我深信,女孩會覺得很有趣,變得愛我,如果我F。例敢於吃很多噁心的東西。它總是有東西在它和雲雀的時間。我有不少遊戲的精力和是-也許現在仍然是-這樣的人,他們想給一個適當的燈泡。在高中這是一件抽煙,喝啤酒。而且我發現,我是能夠讓自己集中所有的時間和女孩子可以看出。它必須曾經因為是我生命的標誌“。LM:“我搜索到的內容和實質。從事戰鬥的鯨魚和東西。在現實中,它是確實是一件讓生活兩步和詩歌它來代替。因為我發現,存在於當下很難,你想想的Mads什麼呢?LM:“令他深感膚淺,不明白的是什麼生活。哈!“ 你什麼時候發現對方了嗎?MM:“高中畢業後,我想”。LM:“我是一年級學生的Mads。事實上,我去五年高中,因為我抽煙這麼多雜草。我被拋出兩次。“ MM:“作為回報,一個優秀的考試。我才勉強。“ 這一定對您影響小兄弟大哥畢業前?LM:“是的,這不是很滑稽。但是,如果沒有得到太多到它,它呈丁
翻訳されて、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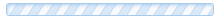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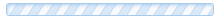
Lars和馬斯Mikkelsen出生,是一個,每隔一年半。 他們已走到同一學校,和作為兒童他們各自的最好的朋友。 作為成人他們選擇了同一訓練,主演,每隔一年。 但是,它們是不同了——無論在個人和作為行動者。
實際Lars Mikkelsen,36年,是高及瘦。 你的臉是狹隘和標示Sharp zygomatic骨和激烈,灰藍色的眼睛。 ,即使他是這樣安靜和友好的一般商業休閑裝),你可以很好地理解,其實這是他,是選擇方面發揮著主要作用,他說:「吸」在劇場在1995年。
實際Lars Mikkelsen,特別是集中在戰區,因為他離開teaterskole在1995年的國家。 他一直參與一系列廣泛的意見,除其他外,該劇院和小,實驗劇場,bådteatret和情感萬花筒在哥本哈根,直到他他後來成立了一個兩年前在皇家劇院。
實際馬斯米克爾森,僅10吋少於其大兄弟和加強建立。 halvlange backswept鋸齒翅膀的,可以使頭發剃發和他drenget和一個小勇氣來看。 並輔以一些好、棕眼,一個廣泛和敏感口和高zygomatic骨他看上去像十全十美的一個真正的“心臟搏動ugebladsopskrift til”和英雄人物。
實際現在不幸的是死者Lars kaalund每先生提出“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煤氣廠,它是羅伯特·羅密歐,拿到的作用。 他是連接到周圍的電路Dante博士和煤氣廠。但由於航班從skuespillerskolen在奧胡斯劇院在1996年,他主要集中在拍電影,是當今的尼古拉斯線圈refns"固定"行動者。
實際mm:“有一些形式的戰區,我根本不想。 我認為,例如可以很有趣地發揮霍爾伯格、伊普森和莎士比亞的傳統意義上的任期。 這是因為我有什麼問題都不反對書,就是這麼少,他們將列在一個方法,我關注。 作為一個規則的溺斃的技術和“讓我們現在終於被完全停止,當我們發揮莎士比亞的方式,因為這是一些漂亮的說話!」但莎士比亞,當然,簡直是骯臟! 為何要這樣可被判罰款和休憩的呢? 我想發揮劇院,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可以認同。 他說:“
實際LM:他說:「我並不稀奇古怪的僵化不formstudier將做出很多。 我本人曾經歷過一個字符串。 他們是一個標志,inderligheden沒有良好背景在丹麥戲劇的時刻。 這一關鍵因素是,影響觀眾,而不是單看東西,在審議階段。 他說:“
實際的話,是 重要
但它是一個巧合,你很難發揮在皇家劇院,雖然馬斯屬於博士在周圍的電路Dante和煤氣廠呢?
“在一開始,它是公正採取甚麼他們可以找到。 但沒有,這當然是沒有的機會。 他說:“
實際mm:“這是一個很大的語言。 我選擇了早期聽那些不能發言T-Y-d-e-L{S}我-G-T,但在談論,老百姓做這種現在最廣泛的,」他說,綁在臉上笑著說。
實際LM:他說:「我非常感動的一些老演員在戰區。 為什麼不隻是當他們走上舞台呢? 當然,他們有很多的經驗,但它也涉及到,有勇氣,離開其作用是由幾個字。 它是一種形式的簡,一旦掌握了,是最終的。 但有的道路是鍍層krukkerier與很多。 他說:“
實際毫米:他說:「我很希望在發言的拉爾斯。 但是,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是框架的數字為真正和接近現實的可能。 這是我最大力推行。 這是表明,它是要求行事方法,在其中的目的是“是”的性質,不,我想,我試著假裝,我知道何種方法是採取行動。 他說:“
實際每一個其他的批評 者
如你是主要相似之處?
實際mm:“我們都是同樣的詩,倍的劇院。 最後,仍是一個,它涉及到我們。 他說:“
實際LM:「所以我們正在參與者。 不斷追緝,使其成為更好。 我們都不想加以密切。 他說:“
實際可以在使用過程中的每一個其他的呢? 是在每個其他的硬批評呢?
實際LM:“不難。 但我們都是相互使用,是的。 我用諸如馬斯,當我提出了“影片”。 我不是在這一波的真實性,增加生產,它感到厭煩。 但是,我的幫助,梅麗莎pejlet我有一個什麼「真的是,為什麼它是如此有趣。 他說:“
實際mm:“在我做「羅密歐與茱麗葉》gasværket Lars,我用的語言工作。 他有一種技術,我可以學到東西從klangmæssigt和tydelighedsmæssigt。 他說:“
實際LM:“但是,如果我們使用其他或每一個最大,它是事實上的疑問,請在地面。 作為一個演員你一直困擾著懷疑的是:它是現在很好呢? 我做的嗎? 他說:“
實際的兩個兄弟是第一個行動者的家庭。他們沒有其他兄弟姊妹長大,在一個政治家庭背景與共產黨。 morfaderen得到他們早日讀俄羅斯文學及其謝爾菲。
實際他母親是sygehjælper,父親是銀行家,但在受雇的工會運動,非常年輕。
實際LM:“這不是一個文化之家。 但有很多的想象力和好的故事。 舉例來說,我們已我們聽到radiospil是很小。 我的父親是最佳的好老hørespil從1950年代,“使反對曲”和“神秘”,這種格雷戈裡的街道被遺棄,付諸表決。 我們聽到你總是,當我們的平房,所以這是一家人聚在周圍kassettebåndoptageren和聽。 他說:“
實際mm:“我可以引述他們使所有“反曲”。 我聽過一天兩次為一整年。在這方面,我可以向所有票數,所有音將響起的心。 他說:“
實際LM:“以後我們這樣做是在同一方式與蒙蒂Python。 我們都有其板和能夠在他們頭的心。 我們是無法忍受,是的。 他說:“
實際一頭 isklump
你第一個內存的第二?
實際mm:“有一段時間後,拉爾斯是一個isklump的頭部。 這是當時我們留在山H."
實際LM:“舉行了一個德尼斯這是完全相同的事件,我想到了! 我很高興剛才下來,並發揮,和我一直很難進行之前,我得到的庭院裡的isklump snotten直線,得到了一個非常血腥的鼻子。 他說:“
實際mm:“Lars,非常難過。 因此,我是直直落,粉碎他們一起,因為他們一直看著他。 ,因此,我當然也在一個isklump頭。 他說:“
實際,但這是你,它的小兄弟,這是保護呢?
實際LM:“羅伯特·一直是敏感的神經。 我是較為脆弱,因此它是公正的。 還記得在學校,在一個第一班,甚至有一個男人踢人。 他說:“
實際mm:“......屐-Jens,是的! 他說:“
實際LM:“......我踢直線與它在nosserne屐。 因此,他是你的銀行。 他說:“
實際mm:“我太踢他。 但我拒絕表明,它受到傷害。 他說:“
實際LM:他說:「我是打破的類別,連同一樣,說哎喲! 他說:“
實際mm:“在許多情況下,當時角色有所改變。 雖然我喜歡一個小兄弟是比你身體較小。 他說:“
實際LM:“我太瘦和ranglet,因此,我將永遠不敢於斗爭。 但這畢竟是一路上。 一天,我想從我,因為沒有,這令我感動。 但我從來沒有想把。這是一個字,因為我有一個困難的時候,管理。 他說:“
實際mm:“你很可能比我更不安全,這是很清楚,當時。 這意味著,例如大量Lars,不論他是在與該組。 我是麻醉漠不關心,如果有一個小組,我想,我想可能需要得到它。 他說:“
實際深藍色的 房間
那麼男朋友呢?
實際LM:他說:「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並不具有同一味。 他說:“
實際mm:“我很遲才抵達的過程中,因為我是很忙,體育。 當我站起來的女童,這幾乎是從一天一個。 Lars一laaaaang青少年時期一個與許多愛好者。 和一個房間髹上,是深藍色的東西,這是最患上抑郁音樂、詩歌和睡眠26個小時。 他說:“
實際LM:他說:「我一直不快樂的愛。 多年來我找到肥沃的土壤中的大多數患上抑郁情緒。 它隻是在最近幾年,它確實是較為容易. 他說:“
什麼對Lars,當他正坐在他深藍色室和人患上抑郁和寫詩,聽取古典音樂?
實際mm:“有缺陷,我們是一個明確的關系的時期。我們並無共同-此外,在一起玩一個小手球更詳細。 此外,Lars發揮crappy當時,雖然我花了所有我的生命,發揮運動。 但我是很難明白是甚麼是怎樣的。 其實我是引起,因為我認為他隻是培育這種承諾的一個“weltschmertz". ”
實際LM:“好了,我沒有當然! 他說:“
實際總 klovnerøv
毫米 :他說:「我是一個總klovnerøv。 我深信,將找到它的女童十分有趣,我與野生,例如,如果我不敢吃了很多事情,令我反感。 這是一直是在與時間和國際滑雪聯合會和麻煩。 我是絕對游戲是大量的精力和——現在仍然是--一個,你想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關於燈。在高中這件事,煙霧和喝啤酒。 我發現我是能夠把自己的全部時間在重點並讓人們看到的女童的。 它有可能得到的標志,我國生活自。 他說:“
實際LM:“我要查找內容和實質內容。 記錄是在爭取鯨魚和種類。 其實這件事,讓他們生活在兩步遠距離和詩文,而不是。因為我發現很難在現在。
實際你想一想Jessica當時呢?
實際LM:“他是表面和深感不明白何謂人生是怎樣的。 醫管局! 他說:“
在什麼時候,每個其他呢?
實際mm:“經過gymnasietiden,我相信。 他說:“
實際LM:“我是第一年後學生羅伯特·。 其實我到5年的高中,因為我吸煙,多哈希。 我被扔了兩次。 他說:“
實際毫米:他說:「另一方面,你有一個偉大考試。 我是公正的,很難。 他說:“
實際它必須有影響,你弟弟前學生是大哥呢?
實際LM:“是的,這是不好玩了。 但沒有得到太多,因為是T
實際Lars Mikkelsen,36年,是高及瘦。 你的臉是狹隘和標示Sharp zygomatic骨和激烈,灰藍色的眼睛。 ,即使他是這樣安靜和友好的一般商業休閑裝),你可以很好地理解,其實這是他,是選擇方面發揮著主要作用,他說:「吸」在劇場在1995年。
實際Lars Mikkelsen,特別是集中在戰區,因為他離開teaterskole在1995年的國家。 他一直參與一系列廣泛的意見,除其他外,該劇院和小,實驗劇場,bådteatret和情感萬花筒在哥本哈根,直到他他後來成立了一個兩年前在皇家劇院。
實際馬斯米克爾森,僅10吋少於其大兄弟和加強建立。 halvlange backswept鋸齒翅膀的,可以使頭發剃發和他drenget和一個小勇氣來看。 並輔以一些好、棕眼,一個廣泛和敏感口和高zygomatic骨他看上去像十全十美的一個真正的“心臟搏動ugebladsopskrift til”和英雄人物。
實際現在不幸的是死者Lars kaalund每先生提出“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煤氣廠,它是羅伯特·羅密歐,拿到的作用。 他是連接到周圍的電路Dante博士和煤氣廠。但由於航班從skuespillerskolen在奧胡斯劇院在1996年,他主要集中在拍電影,是當今的尼古拉斯線圈refns"固定"行動者。
實際mm:“有一些形式的戰區,我根本不想。 我認為,例如可以很有趣地發揮霍爾伯格、伊普森和莎士比亞的傳統意義上的任期。 這是因為我有什麼問題都不反對書,就是這麼少,他們將列在一個方法,我關注。 作為一個規則的溺斃的技術和“讓我們現在終於被完全停止,當我們發揮莎士比亞的方式,因為這是一些漂亮的說話!」但莎士比亞,當然,簡直是骯臟! 為何要這樣可被判罰款和休憩的呢? 我想發揮劇院,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可以認同。 他說:“
實際LM:他說:「我並不稀奇古怪的僵化不formstudier將做出很多。 我本人曾經歷過一個字符串。 他們是一個標志,inderligheden沒有良好背景在丹麥戲劇的時刻。 這一關鍵因素是,影響觀眾,而不是單看東西,在審議階段。 他說:“
實際的話,是 重要
但它是一個巧合,你很難發揮在皇家劇院,雖然馬斯屬於博士在周圍的電路Dante和煤氣廠呢?
“在一開始,它是公正採取甚麼他們可以找到。 但沒有,這當然是沒有的機會。 他說:“
實際mm:“這是一個很大的語言。 我選擇了早期聽那些不能發言T-Y-d-e-L{S}我-G-T,但在談論,老百姓做這種現在最廣泛的,」他說,綁在臉上笑著說。
實際LM:他說:「我非常感動的一些老演員在戰區。 為什麼不隻是當他們走上舞台呢? 當然,他們有很多的經驗,但它也涉及到,有勇氣,離開其作用是由幾個字。 它是一種形式的簡,一旦掌握了,是最終的。 但有的道路是鍍層krukkerier與很多。 他說:“
實際毫米:他說:「我很希望在發言的拉爾斯。 但是,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是框架的數字為真正和接近現實的可能。 這是我最大力推行。 這是表明,它是要求行事方法,在其中的目的是“是”的性質,不,我想,我試著假裝,我知道何種方法是採取行動。 他說:“
實際每一個其他的批評 者
如你是主要相似之處?
實際mm:“我們都是同樣的詩,倍的劇院。 最後,仍是一個,它涉及到我們。 他說:“
實際LM:「所以我們正在參與者。 不斷追緝,使其成為更好。 我們都不想加以密切。 他說:“
實際可以在使用過程中的每一個其他的呢? 是在每個其他的硬批評呢?
實際LM:“不難。 但我們都是相互使用,是的。 我用諸如馬斯,當我提出了“影片”。 我不是在這一波的真實性,增加生產,它感到厭煩。 但是,我的幫助,梅麗莎pejlet我有一個什麼「真的是,為什麼它是如此有趣。 他說:“
實際mm:“在我做「羅密歐與茱麗葉》gasværket Lars,我用的語言工作。 他有一種技術,我可以學到東西從klangmæssigt和tydelighedsmæssigt。 他說:“
實際LM:“但是,如果我們使用其他或每一個最大,它是事實上的疑問,請在地面。 作為一個演員你一直困擾著懷疑的是:它是現在很好呢? 我做的嗎? 他說:“
實際的兩個兄弟是第一個行動者的家庭。他們沒有其他兄弟姊妹長大,在一個政治家庭背景與共產黨。 morfaderen得到他們早日讀俄羅斯文學及其謝爾菲。
實際他母親是sygehjælper,父親是銀行家,但在受雇的工會運動,非常年輕。
實際LM:“這不是一個文化之家。 但有很多的想象力和好的故事。 舉例來說,我們已我們聽到radiospil是很小。 我的父親是最佳的好老hørespil從1950年代,“使反對曲”和“神秘”,這種格雷戈裡的街道被遺棄,付諸表決。 我們聽到你總是,當我們的平房,所以這是一家人聚在周圍kassettebåndoptageren和聽。 他說:“
實際mm:“我可以引述他們使所有“反曲”。 我聽過一天兩次為一整年。在這方面,我可以向所有票數,所有音將響起的心。 他說:“
實際LM:“以後我們這樣做是在同一方式與蒙蒂Python。 我們都有其板和能夠在他們頭的心。 我們是無法忍受,是的。 他說:“
實際一頭 isklump
你第一個內存的第二?
實際mm:“有一段時間後,拉爾斯是一個isklump的頭部。 這是當時我們留在山H."
實際LM:“舉行了一個德尼斯這是完全相同的事件,我想到了! 我很高興剛才下來,並發揮,和我一直很難進行之前,我得到的庭院裡的isklump snotten直線,得到了一個非常血腥的鼻子。 他說:“
實際mm:“Lars,非常難過。 因此,我是直直落,粉碎他們一起,因為他們一直看著他。 ,因此,我當然也在一個isklump頭。 他說:“
實際,但這是你,它的小兄弟,這是保護呢?
實際LM:“羅伯特·一直是敏感的神經。 我是較為脆弱,因此它是公正的。 還記得在學校,在一個第一班,甚至有一個男人踢人。 他說:“
實際mm:“......屐-Jens,是的! 他說:“
實際LM:“......我踢直線與它在nosserne屐。 因此,他是你的銀行。 他說:“
實際mm:“我太踢他。 但我拒絕表明,它受到傷害。 他說:“
實際LM:他說:「我是打破的類別,連同一樣,說哎喲! 他說:“
實際mm:“在許多情況下,當時角色有所改變。 雖然我喜歡一個小兄弟是比你身體較小。 他說:“
實際LM:“我太瘦和ranglet,因此,我將永遠不敢於斗爭。 但這畢竟是一路上。 一天,我想從我,因為沒有,這令我感動。 但我從來沒有想把。這是一個字,因為我有一個困難的時候,管理。 他說:“
實際mm:“你很可能比我更不安全,這是很清楚,當時。 這意味著,例如大量Lars,不論他是在與該組。 我是麻醉漠不關心,如果有一個小組,我想,我想可能需要得到它。 他說:“
實際深藍色的 房間
那麼男朋友呢?
實際LM:他說:「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並不具有同一味。 他說:“
實際mm:“我很遲才抵達的過程中,因為我是很忙,體育。 當我站起來的女童,這幾乎是從一天一個。 Lars一laaaaang青少年時期一個與許多愛好者。 和一個房間髹上,是深藍色的東西,這是最患上抑郁音樂、詩歌和睡眠26個小時。 他說:“
實際LM:他說:「我一直不快樂的愛。 多年來我找到肥沃的土壤中的大多數患上抑郁情緒。 它隻是在最近幾年,它確實是較為容易. 他說:“
什麼對Lars,當他正坐在他深藍色室和人患上抑郁和寫詩,聽取古典音樂?
實際mm:“有缺陷,我們是一個明確的關系的時期。我們並無共同-此外,在一起玩一個小手球更詳細。 此外,Lars發揮crappy當時,雖然我花了所有我的生命,發揮運動。 但我是很難明白是甚麼是怎樣的。 其實我是引起,因為我認為他隻是培育這種承諾的一個“weltschmertz". ”
實際LM:“好了,我沒有當然! 他說:“
實際總 klovnerøv
毫米 :他說:「我是一個總klovnerøv。 我深信,將找到它的女童十分有趣,我與野生,例如,如果我不敢吃了很多事情,令我反感。 這是一直是在與時間和國際滑雪聯合會和麻煩。 我是絕對游戲是大量的精力和——現在仍然是--一個,你想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關於燈。在高中這件事,煙霧和喝啤酒。 我發現我是能夠把自己的全部時間在重點並讓人們看到的女童的。 它有可能得到的標志,我國生活自。 他說:“
實際LM:“我要查找內容和實質內容。 記錄是在爭取鯨魚和種類。 其實這件事,讓他們生活在兩步遠距離和詩文,而不是。因為我發現很難在現在。
實際你想一想Jessica當時呢?
實際LM:“他是表面和深感不明白何謂人生是怎樣的。 醫管局! 他說:“
在什麼時候,每個其他呢?
實際mm:“經過gymnasietiden,我相信。 他說:“
實際LM:“我是第一年後學生羅伯特·。 其實我到5年的高中,因為我吸煙,多哈希。 我被扔了兩次。 他說:“
實際毫米:他說:「另一方面,你有一個偉大考試。 我是公正的,很難。 他說:“
實際它必須有影響,你弟弟前學生是大哥呢?
實際LM:“是的,這是不好玩了。 但沒有得到太多,因為是T
翻訳されて、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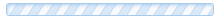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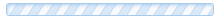
他の言語
翻訳ツールのサポート: アイスランド語, アイルランド語, アゼルバイジャン語, アフリカーンス語, アムハラ語, アラビア語, アルバニア語, アルメニア語, イタリア語, イディッシュ語, イボ語, インドネシア語, ウイグル語, ウェールズ語, ウクライナ語, ウズベク語, ウルドゥ語, エストニア語, エスペラント語, オランダ語, オリヤ語, カザフ語, カタルーニャ語, カンナダ語, ガリシア語, キニヤルワンダ語, キルギス語, ギリシャ語, クメール語, クリンゴン, クルド語, クロアチア語, グジャラト語, コルシカ語, コーサ語, サモア語, ショナ語, シンド語, シンハラ語, ジャワ語, ジョージア(グルジア)語, スウェーデン語, スコットランド ゲール語, スペイン語, スロバキア語, スロベニア語, スワヒリ語, スンダ語, ズールー語, セブアノ語, セルビア語, ソト語, ソマリ語, タイ語, タガログ語, タジク語, タタール語, タミル語, チェコ語, チェワ語, テルグ語, デンマーク語, トルクメン語, トルコ語, ドイツ語, ネパール語, ノルウェー語, ハイチ語, ハウサ語, ハワイ語, ハンガリー語, バスク語, パシュト語, パンジャブ語, ヒンディー語, フィンランド語, フランス語, フリジア語, ブルガリア語, ヘブライ語, ベトナム語, ベラルーシ語, ベンガル語, ペルシャ語, ボスニア語, ポルトガル語, ポーランド語, マオリ語, マケドニア語, マラガシ語, マラヤーラム語, マラーティー語, マルタ語, マレー語, ミャンマー語, モンゴル語, モン語, ヨルバ語, ラオ語, ラテン語, ラトビア語, リトアニア語, ルクセンブルク語, ルーマニア語, ロシア語, 中国語, 日本語, 繁体字中国語, 英語, 言語を検出する, 韓国語, 言語翻訳.
- OK lng po mhie..mkukulit pa rn.
- Reiseknigge Asien: Fettnäpfchen vermeide
- Quiet drive
- 幼女
- 子
- 女性は性的興奮の絶頂でオーガズムに達します
- puto te
- もんだい
- Den nordisk-asiatiske fusion betyder bla
- 糞野郎!!死ね!!
- En grundpakke består af enten ris- eller
- 幼女 無修正
- 兄弟
- 運がよければ
- Yes I already tell to him
- 糞野郎
- 問題
- hi mhie...miss u
- 女性は性的興奮の絶頂でオーガズムに達します
- Enable with UFO main esp (yes you need t
- Reiseknigge Asien: Fettnäpfchen vermeide
- ちんちん ぺろぺろ
- Reiseknigge Asien: Fettnäpfchen vermeide
- Leah del Caduceus